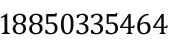转自苏州古建网
苏州有“标志性”的东西是不少,但要作为整个城市的“标志景观”,感觉上好像还是缺了点什么。
不能为大多数市民、为社会公众所“共识”的“标志景观”,其所谓的“标志性”又从何谈起呢?
城市标志景观实质就是“城市之脸”,对苏州而言,或许真的是不亚于城市建设和发展本身的一个相当现实的迫切需求。
称之为“标志景观”,至少要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基本特征:一是视觉性,即好看,有美感;二是识别性,即独特,过目难忘;三是象征性,即喻意鲜明,指代明确,有着高度概括的身份属性。同样,作为一座城市的“标志景观”,当然也必须是具有城市的视觉性、识别性和象征性的景观。比如,北京的天安门、澳门的大三巴、桂林的象鼻山、哥本哈根的美人鱼、伦敦的大本钟,等等。
那么,苏州有这样的标志景观吗?
或说有,或说没有。
说“有”的可能首先列举“虎丘”,这一丘一塔不但有“吴中第一名胜”的名头,还有苏东坡的千年代言:“到苏州不游虎丘乃憾事也! ”更何况还有寒山寺,还有范仲淹塑像,还有苏州博物馆,还有曾被网上评为全国十大城市标志建筑之一的苏州园林……,苏州的“标志景观”不要太多。
说“没有”的当然也少不了会有诸多的理由,比如虎丘塔的识别性,寒山寺的宗教性,博物馆的简约性,苏州园林的相似性,历史人物的模糊性,等等,显然都不同程度的影响到了城市“标志景观”的完美构成。苏州有“标志性”的东西是不少,但要作为整个城市的“标志景观”,好像还是缺了点什么。
作为一座城市的“标志景观”,除了要具有视觉性、识别性、标志性等功能属性外,还必须强调一个以“共识性”为前提的社会属性,即必须要获得社会的公众性的普遍认同,而不是部分的认同。道理很简单,城市是全体市民的,甚至也可以说是社会公众的。不能为大多数市民、为社会公众所“共识”的“标志景观”,“标志性”又从何谈起呢?
不过,通观中外城市“标志景观”的形成和确立,好像也从来没有某种既定的形成“共识”的方式和途径。自然天成的有之,约定俗成的有之,刻意打造的也有之,“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更有之。这大概也是之所以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城市却并没有那么多相应的城市标志景观的原因所在。
延安的宝塔山,山不算高,也就一千多米,塔也不老,只是个明代建筑。但自毛泽东进了延安,这一塔一山就成了这座城市乃至中国革命圣地的标志和象征。
上海的城市历史虽然不长,但上海却是我国城市标志景观最为著名的城市之一。外滩的万国建筑群,特别是外白渡桥和上海大厦合二为一的经典形象,曾经是几代人心目中挥之不去的大上海印记。而改革开放以后,高高耸立于浦东陆家嘴地区的东方明珠塔又一次给人们带来了全新的视觉冲击。与紧邻的金茂大厦和环球金融中心相比,东方明珠塔虽然不是最高,但她却能成为与周边的建筑群落交相辉映的视觉中心,华丽地展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大都市的壮观景色,从而成为无可争议的改革开放的大上海的城市标志景观。
法国的埃菲尔铁塔于1991年即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也是巴黎最著名的城市标志景观。但埃菲尔铁塔这样的美誉实在是来之不易。从设计到施工,埃菲尔铁塔一开始就遭到了大部分巴黎人的拒绝和反对,城市建设和规划的专家们更是给予了无情的嘲笑和尖刻的批评。即使在埃菲尔铁塔落成之后,批评、反对甚至以示威请愿的方式要求拆除的声浪也始终没有停息。侥幸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埃菲尔铁塔在无线电通讯联络方面为法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人们因此对她刮目相看,并由嫌弃、憎恨逐渐地转变为欣赏和爱护有加。这一不平凡的经历也使得埃菲尔铁塔比巴黎圣母院和凯旋门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更为风头。
1992年6月,深圳人民怀着对邓小平同志的敬仰和感激之情,制作了一幅《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的巨型画像。画像位于深南中路,高10米、宽30米。邓小平同志亲切的微笑、深圳现代化的宏伟场景和飞翔的红杜鹃组成了一幅生动感人的画面,象征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与以“深圳速度”为代表的中国经济奇迹的密切关联。这幅画像如今已和深圳市政府的“孺子牛”雕塑同为公认的深圳城市标志景观。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城市标志景观史上,深圳的邓小平画像,无论是内容、形式还是影响,相信绝对是史无前例、绝无仅有的。
“城市标志景观”虽然往往只是一幢建筑、一座雕塑,或者是一处人文的胜迹,一处自然的风光,但它的作用和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却可以涵盖甚至是超越城市的本身。更确切的说,城市标志景观实质就是 “城市之脸”。而“城市之脸”则是“城市如人”的理念延伸。 “脸”与“人”的关系不但是对应的,也是惟一的;不但是静态的,也是动态的;不但是外表的,也是内在的;不但是现实的,也是历史的。所以,不管怎么说,不管有多少难以确定的因素,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已经进入了“城市时代”的今天,拥有一张魅力四射、气质超群的“城市之脸”,对苏州而言,或许真的是不亚于城市建设和发展本身的一个相当现实的迫切需求。
来源:苏州日报


 未认证
未认证
 客服1
客服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