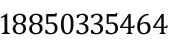在距离清西陵以北100多公里的北京紫禁城午门,斜风细雨,人潮涌动。昔日皇家用于宣旨、征讨、献俘、行刑的午门广场,几乎每天都要被世界各地的游人踩踏,石砖已残缺不整。另一群“匠人”在小雨中忙碌着,他们要替换下破败的石砖,让这座广场重现威武气派。
两群“匠人”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古建修缮工人。
《管子·小匡》曰:“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他们是名副其实的“工”,曾是一支庞大的社会群体。如今,这一群体及其手中安身立命的根本——古建修复技艺正随着时间的消逝走向没落,而这些将被历史洪流淹没的技艺,也影响着古建保护。
“这一行,50多岁算年轻人”
呲、呲、呲……崔师傅用特制的刨子将不规整的微型椽子削圆,面露苦笑:“再不学,这一行的手艺就失传了!”他是一名从事古建修复行业十余年的木工,正和另外两名年龄相仿的伙计一同完成一件山西洪洞县广胜寺明应王殿木制模型。
这件模型比真实建筑缩小了20倍,是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的项目,崔师傅说,制作这样一个模型,他们三个人要用40天、每天9个小时才能完成。
“虽然工资不高,但还是要把这些留下来”,崔师傅身上有一种责任感,“年轻人都不学了,50多岁的可以算年轻人了!”他将自己划为古建修缮行业的新手。
“复杂!古建修缮太复杂了”,北京建工六建古建分公司总工程师曾安宁说。“搞新建,你就照图施工;搞古建,图纸就一句话‘照传统工艺施工’,这句话太重了!”曾安宁1969年参加工作,搞了27年新建,20年古建,深知个中甘苦。在他看来,古建修缮行业之所以缺少新生力量,与古建的复杂程度密切相关,“干着农民工的活,操着工程师的心。”
“其实,凡是技术工人都多多少少存在这个问题,大家都愿意当白领,不愿意当工人。而古建修缮由于自身局限性,吸纳的年轻人更少。”曾安宁介绍,在公司的修缮设计部门还有为数不多的年轻人,而在施工单位,这一数字简单直接:0。
“干这一行,没有韧劲儿不行、怕苦怕累不行、不感兴趣还是不行!”古建分公司油饰彩画工长程玉林在午门广场施工项目前对记者说。62岁的他被公司返聘,迄今有43年古建修缮经验,“不回来真不行啊,没人接得了我的活儿,总不能看这行完了吧?”他满面愁容地说。“难道只能靠返聘的老人撑着吗?”程玉林曾收过3个徒弟,其中只有一个还在从事这个行业,但也即将退休了。
“很多师父把手艺带到棺材去了”
师徒制,是文物修缮行业的规矩。古建分公司副总经理乔振来在崇陵妃园寝指着正殿上脱落的绿瓦说:“这个瓦的坡度很重要,到了某一个地方,一定要抬一下,否则就没有神韵了。”他对记者说,古建修缮有很多窍门,只能通过师徒制的口传心授来实现,“一些东西就是师父一句话的事儿,凭这个就能吃一辈子。但很多师父都把窍门带到棺材里去了!”
靠师徒制维系的技艺传承,虽然牢靠,但有损耗。曾安宁说,“教会徒弟、饿死师父”的理念在这一行里仍然根深蒂固,“我刚入行时,师父把基本的东西都教给我,但他磨水刷石、干粘石的时候,会将我支走,回来后,他干完了。”师父对徒弟“留一手”,让很多世家出身的工匠占到了便宜,“因为师父不会跟自己儿子有保留。”
师徒制有局限性,但其口传心授和实践性却是其他方式难以比拟的。近年来,随着国家文物部门对文物保护重视程度的提高,从事古建工作的项目经理、工长、工人都要进行培训,持证上岗,这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古建修缮。但这种培训,仅仅是一个敲门砖,“修缮、修缮,拆开看!”乔振来说,“成为一名合格的匠人,只能靠修缮现场的无数次经验积累。”
与古建修缮实践同时展开的,是古建学术研究,但这些研究还停留在理论层面,与修缮实践脱节。程玉林讲述了一段亲身经历,2011年至2013年故宫慈宁宫花园整修期间,由于年久失修,咸若馆前抱厦的4根柱子均出现了向外倾斜的状况,幅度最大达到15厘米,专家论证一年后也未敢签字。最后还是施工方采取了快速拨正的方式,迅速解决问题,“这就是经验,有时候见得多、做得多,比学得多、想得多有用!”
“如果这些专家能到施工单位待一段时间就好了!”曾安宁感慨,现有古建理论只是知识分子对部分工匠经验的总结、提炼,而实际上他们并不是实际操作者。
“还是要寄希望于年轻人!古建修缮已经出现人才断档了,缺口不能再大了。”曾安宁观察到,“目前20多岁的年轻人是没有的,30多岁的凤毛麟角。这一行至少断档10年!”
“形”易模仿,“神”难兼备“古建讲究规制,主殿高于配殿,东配殿高于西配殿”,乔振来说,“但我看过一个皇陵,配殿油饰彩画比主殿修缮得精美许多!”普通游客一掠而过的东西,在乔振来这样的行家眼中沦为不伦不类。
“合规矩”,是所有古建修缮者的执念。“前几年编《工法》,要求有新工艺,我当时就反对:古建修缮必须遵循古法,不允许你有创新!”曾安宁说。“修北京法源寺的时候,施工队被我轰走三拨,他们干出来的不是那个东西,那是糟蹋文物,看着心疼。”程玉林也对古建有种难以动摇的情感寄托,“外观上能看出古建的意思,但就是修不出那个味儿!”
程玉林所说的“味儿”是古建的神韵。“有些东西,放个三年五年,谁都看不出来,往往过去三五十年,才分高下。”曾安宁说,古建承载的是历史,而历史又是检验古建修缮的最好标准,“所以,干这一行,最重要的其实是良心!”

但是,传承不是因袭,“遵循古法的改造,也是对得起良心的事情”,曾安宁特别强调。实际上,中国古代建筑也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以北京为例,明代到清代的建筑,是经过逐步改造的。曾安宁介绍,长期在一线修缮现场就可以发现,一般情况下年代越靠后,受力形式就越趋向合理,油饰彩画就越丰富多彩,表现人性化的东西就越多。“实际上,每一代人都有表达自己思想的权利,但前提是,你一定要充分理解你的祖先。”曾安宁说,这是他辗转新建、古建领域,花费大半生体悟出的道理。
“手攥成团,落地开花”,这是古建灰土的配置标准,“但具体成分比例是多少?古人没有这个概念,你只能用心去体会。”乔振来说,这是他理解的“味儿”,“还真别小瞧这些黏合材料,外面看不出来,但灰土砌出的墙就是有混凝土砌不出的神韵。”
“一些传统被推翻了,‘神韵’也就不复存在了,再往后,古建也就只剩下那一层空壳。”曾安宁说,近十年来国家加大了文物保护力度,但古建修缮仍遭遇着不少困境,一些真正遵循古法的传统工艺在市场环境中挣扎图存。“拿一块砖举例,按照传统工艺烧,就是6至7元钱,这明显比造价5元的砖吃亏,所以很多厂商都把一些必要的工序简化了”,曾安宁说,修缮故宫用的金砖,在北京已经买不到了,要到南方去买,“即使这样,东西也和原来不一样了……”
午门前细雨渐止,程玉林要带着施工队忙活了。3年前,他所在的团队成功解决了午门雁翅楼“尿檐”问题,根治了雨水侵蚀檐体的顽疾,“但愿古建修缮这个行当里,有我一号。但愿以后这一行,修出的还是那个东西。”
乔振来望着清西陵崇陵妃园寝,他们即将在这里动工,一年后,破败的坟冢就将焕然一新。“人在,手艺在;手艺在,古建在”,西陵依傍的永宁山即将吞噬一轮红日,园寝里残败不堪的绿琉璃瓦即将映衬的是点点星光……


 未认证
未认证
 客服1
客服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