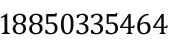读懂陈从周
著名古建筑学家、园林学家,现代中国园林学开创者、奠基人,现代中国园林艺术集大成者——这是世人对陈从周的普遍认识。这一盛誉毫无疑问。早在1956年,他便出版了中国当代第一部园林学专著《苏州园林》,引起全国建筑界的关注。此后成果不断,直至《说园》出版,已是热到洛阳纸贵了。他的足迹遍留江苏、浙江和山东。有人戏称他是“两江总督”,即江苏、浙江古建筑的大总管。1980年,陈从周以苏州网师园殿春簃为蓝本,为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修建了明式庭园“明轩”,以小见大、移步换景之功让美国人为之倾倒,一时间甚至在全世界掀起了中国文明热。此外,他还主持建造了宁波天一阁东园、上海豫园东部、昆明楠园等,无一不是深谙中国园林之道的精髓之作。
然而,把陈从周仅仅视为园林、古建筑学家是不全面的。事实上,他从事园林是“半路出家”。陈从周的本行原是文史,21岁时他考入之江大学主修文史,在此后修复园林、古建筑的工作中,历史始终是他最重要的依据和目标;他还是散文家,先后编辑出版了《书带集》、《春苔集》、《帘青集》等,今天人教版中学语文课本中的《说屏》便是他的名作之一;他师承张大千先生,早在上世纪40年代便蜚声上海画坛,到80年代,他的画还被列入国宝之列,禁止出境;他酷爱戏曲,与昆曲大师俞振飞先生亦师亦友——陈从周83年的生命中,前30年如同学术界的“花花公子”,涉猎的学问既博且专,古今、中外甚至文理兼修,书画、诗词、散文、鉴赏、文史、戏曲等,都是大师级的。只是,这许多成就都被他在园林学上的成就掩盖了。

其实,陈从周投身于中国园林事业中,只是为自己所钟爱的传统文化找到了一个最合适的载体,似乎也只有园林可以如此完美地承载美术、雕塑、建筑、词赋、文史和曲艺。于是,陈从周的人生便恰如他笔下的苏州园林:绚烂之极归于平淡。33岁之年,他皈依了中国园林并为之抗争至死。
“名园不可失周公,处处池塘哭此翁。多少灵峰痛米老,无人再拜玉玲珑。”这是陈从周先生去世后,他的好友、著名红学家冯其庸先生写的悼亡诗。陈从周确是中国园林之幸,而从某种角度看,能遇到园林才是陈从周之福。
老夫依旧汉儒生
“老夫依旧汉儒生”,这是陈从周对自己的总结,充满自豪之情。说起来轻松,然而,当我们将人物放到20世纪中国的大背景下,这句话便显出了言者的巨大勇气和对民族的极大热爱。从某种角度上说,陈从周是个“不合时宜”的人,似乎落后保守,其实超越时代。
陈从周一生坚持尊师重教,即使在十年浩劫中,他也多次冒着风险,为过世的老师送上挽联。80岁那年,老师王遽常九十岁祝寿会,当时暴雨雷鸣,他为按时赶到,一大早就动身,并以中国传统中最为隆重的叩拜大礼为老师祝寿。
陈从周的第一本书其实是《徐志摩年谱》。陈从周自幼崇拜徐志摩,两家又是姻亲,手边原始资料越积越多,为徐志摩立传的工作已经非他莫属。1947年开始,陈从周用业余时间编撰年谱,完稿时已是1949年5月,时局动荡,许多朋友都劝他不要再干这蠢事。陈从周请赵景深先生作序,他不肯写,而徐悲鸿先生则要他研究鲁迅。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此书,陈从周费尽心思找到一家印刷厂,自费印成了500本,还答应免费为印刷厂工人上夜课。“文革”中,陈从周果然因为“为反动诗人徐志摩树碑立传”定下罪名,受到了批斗。对于这个所谓的罪名,他不仅问心无愧,简直觉得引以为豪,他说:“我是‘活该’,我只觉得做了一件正确的事。”半个世纪后,这本最初无人问津的书渐渐显出了它的内在价值。此后包括《辞海》在内的几乎所有研究、撰写徐志摩生平和传记的文字,都是以陈从周的《徐志摩年谱》为蓝本。
全国大炼钢铁的时代,有人要拆苏州城墙,用墙砖砌小高炉。陈从周坚决反对,振臂疾呼,他说,苏州这座有2500年历史的文化古城,城墙上的每一块砖都是文物。当时北京批判梁思成,陈从周也被作为中国营造社的外围分子加以批判。在一场讲座中,他又乱说话了:“虎丘山只有三十多米高,为了领导人来,造了一条公路。领导两万五千里长征都走过,莫非这样一座小山都上不来?他们来是要游的,不是来走马路的。”他被扣上了“诬蔑共产党、丑化领袖”的帽子,自此成了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老运动员”。
但陈从周一直没学“乖”,对于自己坚守之处,他总是不可抑制地表现出“汉儒生”固执的一面。
1986年,上海市政府决定重建豫园东部,请陈从周主持工程。这是一个工作量很大、规格极高的园林工程。工程的难度在于,它不是新建,而是修复补建,如同一座名园的续篇。豫园的历史既是一种提示,也成了一种束缚。这时,陈从周已近70高龄,他同意接下这份工程。但同时又郑重地说:“我不要报酬,也不要车马保驾,我要的是指挥权。”在陈从周看来,工程最大的困难是官僚作风,在没完没了的行文、盖章下,有时为移树一类的小事,可能要等上一年半载。陈从周放弃了设计费和施工指导劳务费,两笔款项加起来,在当时可谓天文数字。为了豫园,他几乎是以一种空前绝后的方式取得了指挥权。
最终,豫园东部重建工程,从构思、设计、施工、选材、工艺都是他一人把关,每个工匠都经过考试选拔,工匠们每造一部分,他都仔细检查,不合要求的哪怕已经施工完的地方也必须拆掉重来,直到完美。
1918年,陈从周出生于浙江杭州。父亲为他取名郁文,字从周。名字来源于孔子对自己心目中理想社会的描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取这个名和字,是希望孩子的一生文才馥郁。父亲在陈从周8岁时病逝,只给他留下6个字的手书“毋忘水源本木”,这张条幅挂在家中堂上,陈从周日日看见,时时思考,年复一年地重新理解着这6个字。直到垂老,陈从周依然不能忘记这句话。
陈从周小学、中学、大学都就读于教会学校,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近乎于执拗。他一生喜爱穿着汉民族服装,常常是对襟褂子,布鞋一双。他不看外国电影,不听西洋音乐,对国人曾有的“出国热”大为不满。两个女儿请他去法国、美国居住,他说“我死也死在中国”。对国人不愿饮茶而好饮料大加讥讽,说“饮”字之下加一“料”字,与肥料、废料一样不讨人喜欢。
改革开放,当西方文化冲击中国时,他利用一切机会,为继承和弘扬东方文明摇旗呐喊。他的研究生,报考面试时都要加试一门“百科知识”。学生记笔记要用毛笔,写字要用繁体,而且还要竖写。他授课从不照本宣科,他与学生谈人生、谈文学,还要求学生们都要听昆曲,喝绍兴酒,外国留学生也不例外。他自掏腰包请学生看昆剧,体味古园林建筑与昆曲在艺术趣味上的亲缘关系。
浙江海盐县境内的南北湖,陈从周曾撰文赞称:“比扬州瘦西湖幽深,比杭州西湖玲珑,能兼两者之长。”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南北湖周遭的工业、商业建筑用石需求大增,不少山民建起石厂,不分昼夜地炸山取石。陈从周听说后,不顾七十多高龄,冒着初冬的严寒,急急赶往南北湖。到达景区后,陈从周震惊了。山体千疮百孔,植被毁坏严重,更有人在山上捕捉珍禽异鸟,禽鸟几乎绝迹。
当地领导请陈从周吃饭,菜上桌时,看到一盘野味黄鹂,他愤而离去,从此开始了无休止的奔波呼吁。嘉兴市领导请他写字,他写的是“救救南北湖”。为海盐市领导作画,他的画上题了一句“在隆隆炮声中挥泪写之”。他前往上海市政府,希望政府出面阻止企业购买南北湖的石料。他还免费指导南北湖旅游建设,觉得只有景区建设起来,南北湖的百姓才能子子孙孙真正地靠山吃山。
他说:炸山采石是短命做法,这哪里是靠山吃山,这是在吃子孙后代的饭!他又说:振兴中华,必先绿化。他觉得,遵循“自然”是中华文明的核心之一,毁绿就等同于抛弃传统文化。
直到1991年,陈从周在报上看到《南北湖自然风景区炸山捕鸟何时了》的读者来信,忍不住拍案而起,向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告了“御状”,南北湖风景区十三家石矿厂终于关停。今天,它已作为上海的后花园,成为旅游胜地。
这个时期,在“文革”中幸免于难的古典园林建筑,却在经济浪潮和大拆大建中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自然生态和人文景观遇到灭顶之灾。陈从周像“救火员”一样,四处“劫法场”,不少人恼他恨他。在散文《故居》中,陈从周劝道:“历史文化遗迹,我们不能破坏得太多,可保留的应该保留,给人们有个寻根的地方。我曾听得一个归侨说:祖坟挖掉了,祖宅毁掉了,家谱烧掉了,还有什么值得我寻根之处?想法过头一些,但亦应该认识这是人之常情。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古人这话并没有过分。”
暮年,为了力保上海徐家汇藏书楼,陈从周中风倒下,从此一病不起,逝于2000年。
在中国变化最为巨大的20世纪,陈从周始终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式文人,他一生的夙愿只有一个:希望中国“把根留住”。
今天的中国发展得更加理性了。有人正极力保护、传承着代表文脉的点点滴滴,但另一方面,承载着古中国文明的城镇、建筑、景色仍在遭受破坏,渐渐消失、渐渐庸俗。我们作为后人,必须读懂陈从周,了解他为之自豪的事物、为之奋斗一生的理由。这是陈从周用自己的一生留给我们的思考题。


 未认证
未认证
 客服1
客服1